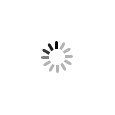《数码宝贝》同人文 回忆的诗
就是这样被欲望所打败,我趁着妈妈出门的空档,利用神圣计划进入数码世界,乘着进化了的比多兽飞往美国的数码世界大门位置。
穿过大门,我见到了时隔一年多未见的美美,她的脸上是和我一样的欣喜。
看到许久不见的她我反而局促起来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傻傻的站在那,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是谁先笑出了声,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哈哈的笑了起来。
那是我上国中以后,第一次这么开心的笑。
那天美美准备了她新学会的三明治给我吃,或许是第一次做,说实话味道并没有很好,但我还是把它全都吃光了。
那天我们就像第一次通话时一样天南海北聊了很多,那份心情我无法忘却。
那天…我好像还悄悄拉了她的手。
那种触感,我无法忘却…
后来当我想第二次通过数码大门去往美国时,由于邪恶数码兽的作怪,数码大门再次关闭,持有旧版神圣计划的我无法再随意进入数码世界。
我和美美又回到了仅仅靠现实世界那一丝微弱的无线电波牵扯着的状态。
每天互发消息好像已经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我的内心。
想念的时间每天都在增加,我不知道我还要这样想她想多久。
e-mail草稿箱中没有收件人的信越来越多,我好想,好想把自己的这份心情告诉她。
就在某天,我鼓起勇气准备打电话告诉她隐藏在我内心多年的秘密时,她发来了一条短消息,说她认识了一个男孩,热情幽默,对她很好,她们经常很愉快的聊天,他叫麦克。
我的手从通话键上移开,那份鼓起的勇气被一盆从天而降的冷水浇灭殆尽。
我意识到,我可能终有一天会从她鲜亮的人生中褪去。
我变得有些任性,假装不在意她发来的信息,故意延迟回复消息的时间,减少每次信息的内容字数,似乎这样是在进行无声的报复。
我多么希望她能察觉到我的异样,多么希望她能在某条信息后加问一句“你怎么了?”,多么希望……
可她没有,她放任着我对她假装的冷漠,她放任着我信息中越来越少的回应,即使我故意只回一个单音节发声词她也放任着不再回复,多少次聊天的话题在我故意的一个“嗯。”中结束。
直到后来……我也放任着她对我发来冷漠的单音节发声词。
我的心已经疼得快要窒息了。
后来我通过联考进入了东京的一所重点高中,那时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和美美联系了,在此之前她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一直被我保存在收件箱里,全文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哦。”。
我不敢删,害怕它将会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话语。
我一直保留着,这最后的回忆。
每当我编辑好想对她发去的信息时,内心就会涌上一股怯懦,促使我把码好的字一个一个的删除。
甚至在庆祝我升学典礼的当晚我都不敢发去问候的信息,而她也没有发来,或许她早已把我忘了。
我,是不是已经从她的生活中褪去了呢?
我不敢去想,也不敢去打扰她鲜亮的人生。
在高中的日子里,没有她,我过得十分安静,安静的上课,安静的读书,安静的回家,甚至鲜少与人交流,埋头在计算机的数码世界里,隔离外界。
寂静的生活吞没了我的一切,太一甚至取笑说我身边的空气都是静止的。我也只是笑着摇摇头,不曾辩驳。
后来由于我沉迷专研计算机程序,电脑水平直线上升,在某次竞赛中被主委会相中推举去参加美国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得到这个消息的我感觉到自己那颗沉寂已久的心又重新跳动了起来,我可以去美国找她了。
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我握着手机,不用查找电话簿,直接依照脑海中的印象按出那串默念过无数遍的数字。我能感受出我很激动,好像又回到了多年前第一次通话的那个夜晚,我看着屏幕的那串数字出神,手指无数次颤动着拂过通话键,却犹豫着,不曾按下。
后来我还是没有打电话给她,第二天醒来手中是被我紧握着已经发烫了的手机,最后我选择关机,坐上了那班飞往有她的地方的飞机。
下了飞机,随行的大赛陪同人员带着我和其他参赛选手入住了酒店,办理了各种手续,同时告知了我们各种注意事项。他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有听清,只知道自己一心只想快点见到那个一直牵挂在心的粉色宽边帽女孩。
在获得自由活动允许时,我第一时间离开酒店,按照她曾经寄来明信片上的地址打车寻找过去。
一路上经过大街小巷,商店街广告牌灯红酒绿,我想象着她背着包轻巧的穿梭于中,走过一幢幢楼房的样子,寻找着她生活的气息。
可是上天好像在和我开玩笑,等我找到地址上的地方,敲门却没有人回应,这时附近的邻居告诉我,太刀川一家回国探亲去了。
我记不得我是如何在邻居诧异的眼光中跌跌撞撞地离开的,我只记得我疯了一样的拿出电话输入那串熟悉的数字拨通,在一阵嘟嘟的等待声中转为忙音,反复了好几遍后突然意识到,对啊,现在这里我的白天是她的黑夜,我忘了,我与她擦身而过了。
最后我发了信息给她,同样也发给了她的好友素娜。
深夜回到酒店,同一间房的另一名参赛者已经鼾声大作,而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拿出手机反复翻看收件箱中保存的她的短信,我的眼睛就被涌上心头的泪水模糊了。
正在我埋头偷偷擦拭眼泪的时候,手机响起了为她设置的特别铃声,我讶异着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颤抖着接起电话,小心的喂了一声。
“喂,好久不见,光子郎。”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数码宝贝大冒险tri.专区
-

AI少女绘:迷你裙 热裤 简单利落展现感性曲线 -

高达之父呼吁年轻人立志打倒宫崎骏:我是没办 -

网友还原《芙莉莲》束缚名场面 你看起来有点 -

《咒回》“我打宿傩”梗图发展到现在 最强的 -

日本动画师自曝低到离谱的薪资 网友:怎么活 -

《樱桃小丸子》声优去世:与鸟山明同时期的人
- 又一盗版动漫网站宣布关停 或涉及DMCA及版权问题0
- 《罗小黑》角色原型被弃养 网友怒骂:吃猫血馒头0
- 《龙与虎》声优遭炎上爆破:受害者有罪论不可接受0
- 万代打造IP“元宇宙” 前所未有的交互空间来袭0
- 《宝可梦:地平线》公布新OP IGN称或许为系列最佳0
-

AI笔下的美女:丝袜什么的不重要 傲人曲线秀出来 -

AI笔下的美女:可爱萌妹 火辣御姐 超棒身材看不够 -

AI笔下的小姐姐:万物复苏 好身材也要尽情展露 -

AI笔下的美少女:超劲爆身材很养眼 还有可爱猫猫 -

AI笔下的风情美少女:忽略小细节 老婆还是那么完美 -

AI绘制超棒美少女 梦寐以求的绝美身材真是太可了
-
类型:动作游戏大小:0 KB
-
类型:卡牌游戏大小:600.00 MB
-
类型:养成游戏大小:0 KB
-
类型:动作游戏大小:3.60 GB
-
类型:角色扮演大小:3.30 GB